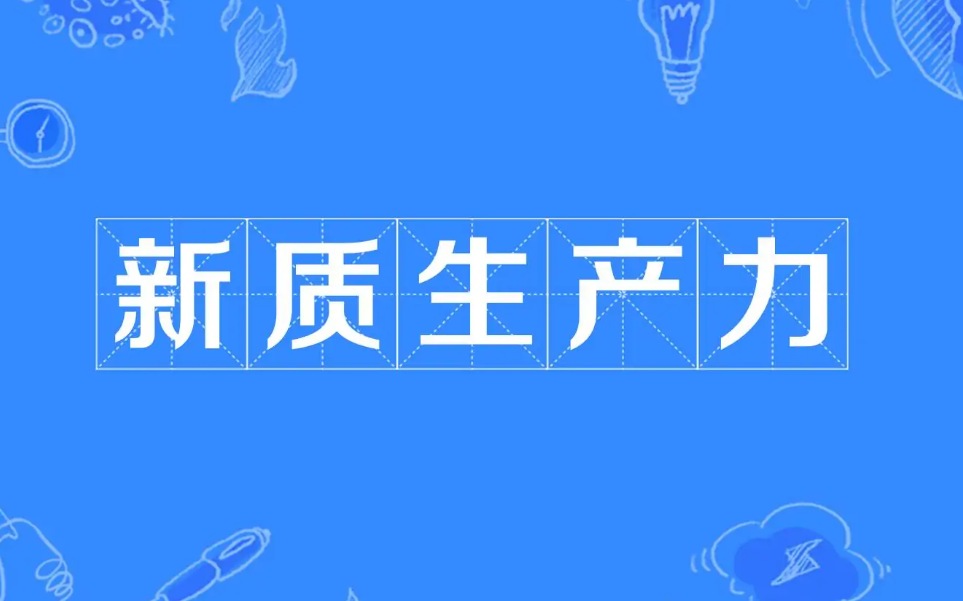
工業(yè)革命以來(lái),生產(chǎn)力經(jīng)歷了五次大的范式變革。每一次生產(chǎn)力范式變革都由科技革命驅(qū)動(dòng),大多歷時(shí)半個(gè)世紀(jì),經(jīng)歷“兩期四段一轉(zhuǎn)折點(diǎn)”,其中“兩期”指新范式導(dǎo)入期和展開(kāi)期,“四段”指導(dǎo)入期的爆發(fā)階段、狂熱階段和展開(kāi)期的協(xié)同階段、成熟階段,“一轉(zhuǎn)折點(diǎn)”即從導(dǎo)入期到展開(kāi)期的大轉(zhuǎn)折點(diǎn)。第五次生產(chǎn)力范式變革即ICT生產(chǎn)力范式變革,始于1971年,到2021年已經(jīng)50年。2020年代迎來(lái)第六次生產(chǎn)力范式——新質(zhì)生產(chǎn)力范式——導(dǎo)入期的爆發(fā)階段到狂熱階段轉(zhuǎn)折點(diǎn)。
新質(zhì)生產(chǎn)力范式既不是單純的綠色生產(chǎn)力范式,也不是單純的數(shù)智生產(chǎn)力范式或者單純韌性生產(chǎn)力范式,而是綠色生產(chǎn)力范式、數(shù)智生產(chǎn)力范式、韌性生產(chǎn)力范式的綜合,即綠智韌綜合生產(chǎn)力范式。新質(zhì)生產(chǎn)力就是綠智綜合偏向的生產(chǎn)力。這既是數(shù)智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的客觀要求,也是全面綠色轉(zhuǎn)型的內(nèi)在要求。一方面,數(shù)智既有發(fā)展路徑是高耗能、高耗水、高碳足跡的,也可能帶來(lái)不確定性。另一方面,數(shù)智技術(shù)可以降本增效、保證精準(zhǔn)治理,可以克服主體之間、要素之間、過(guò)程之間、地域之間的距離和分割,實(shí)現(xiàn)全主體、全要素、全過(guò)程、全地域智能感知、互聯(lián)互通,有效支撐全面綠色轉(zhuǎn)型,提升適應(yīng)韌性,是全面有效綠色轉(zhuǎn)型不可或缺的強(qiáng)大支撐。
新質(zhì)生產(chǎn)力范式根本不同于第一次至第五次生產(chǎn)力范式。后者都以化石能源技術(shù),印刷、電和電子信息通信技術(shù),傳統(tǒng)能源驅(qū)動(dòng)的交通技術(shù)動(dòng)態(tài)結(jié)合為基礎(chǔ);以“資源—產(chǎn)品—消費(fèi)—廢棄物”單向線性流動(dòng)為物質(zhì)代謝典型模式;以機(jī)器為關(guān)鍵生產(chǎn)要素;以工廠化、專(zhuān)業(yè)化、規(guī)模化、效率至上為法則;具有內(nèi)在的不可持續(xù)性,可視為工業(yè)文明的不同生產(chǎn)力范式。與此根本不同,綠智韌綜合生產(chǎn)力范式以可再生新能源技術(shù)、智能網(wǎng)絡(luò)通信技術(shù)、新交通技術(shù)的動(dòng)態(tài)結(jié)合為基礎(chǔ),以可無(wú)限循環(huán)利用的信息資源——數(shù)據(jù)——為關(guān)鍵勞動(dòng)對(duì)象,以人工智能為勞動(dòng)工具,以“資源—產(chǎn)品—消費(fèi)—再生資源”循環(huán)流動(dòng)為重要物質(zhì)代謝模式;堅(jiān)持適應(yīng)韌性、協(xié)同創(chuàng)新、開(kāi)放共享,強(qiáng)調(diào)不斷增強(qiáng)生產(chǎn)力系統(tǒng)的動(dòng)態(tài)適應(yīng)、協(xié)同創(chuàng)新、開(kāi)放共享的能力。因此,綠智韌綜合生產(chǎn)力范式具有內(nèi)在的可持續(xù)性,是一種生態(tài)文明的生產(chǎn)力范式。
最佳生產(chǎn)力布局是生產(chǎn)力范式的空間表現(xiàn)。與前五次生產(chǎn)力范式不同,第六次生產(chǎn)力范式以可再生新能源技術(shù)、物聯(lián)網(wǎng)通信技術(shù)、電動(dòng)交通技術(shù)的動(dòng)態(tài)結(jié)合為基礎(chǔ),以數(shù)據(jù)為關(guān)鍵勞動(dòng)對(duì)象、以人工智能為勞動(dòng)工具、以循環(huán)流動(dòng)為物質(zhì)代謝特征,以適應(yīng)韌性、協(xié)同創(chuàng)新、開(kāi)放共享為法則,同時(shí)勞動(dòng)者創(chuàng)新化和閑暇化。從筆者所倡導(dǎo)的新空間經(jīng)濟(jì)學(xué)來(lái)看,這必然使第六次生產(chǎn)力范式的最佳生產(chǎn)力布局模式表現(xiàn)出四方面的基本特征。
一是隨著綠智綜合生產(chǎn)力范式變革從導(dǎo)入期到展開(kāi)期的演進(jìn),物的智能化再生產(chǎn)與人的再生產(chǎn)空間共聚程度經(jīng)歷先上升達(dá)到一定水平后轉(zhuǎn)而下降的倒“U”型曲線變化,即物的智能再生產(chǎn)在導(dǎo)入期相對(duì)向人口密集區(qū)域集聚,在展開(kāi)期則背離人口密集區(qū)域而指向擁擠成本最小的生態(tài)韌性區(qū)位。
二是高品質(zhì)地方成為創(chuàng)新—生活一體化的新質(zhì)創(chuàng)新綜合體。事實(shí)上,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(jī)以來(lái),在全球綠智技術(shù)—經(jīng)濟(jì)孕育和競(jìng)爭(zhēng)中,以綠色和數(shù)字技術(shù)為支撐的、創(chuàng)新—生活一體化的新質(zhì)創(chuàng)新綜合體已在一定層次上見(jiàn)端倪。
三是韌性網(wǎng)狀網(wǎng)絡(luò)模式。一方面,這是新范式以可再生新能源技術(shù)、物聯(lián)網(wǎng)通信技術(shù)、電動(dòng)交通技術(shù)的動(dòng)態(tài)結(jié)合為基礎(chǔ)在空間上的必然表現(xiàn);另一方面,適應(yīng)韌性法則要求把適應(yīng)韌性作為優(yōu)化生產(chǎn)力布局的基本原則和維度,動(dòng)態(tài)再平衡在地化、在岸化、近岸化、全球化的供應(yīng)鏈策略。因而,網(wǎng)狀城市群、網(wǎng)狀全國(guó)城市網(wǎng)絡(luò)、網(wǎng)狀全球城市網(wǎng)絡(luò)分布式化特征將更加突出,演化為韌性網(wǎng)狀網(wǎng)絡(luò)模式。
四是物質(zhì)代謝區(qū)位指向變化。可再生新能源既具遍在性又具地方性,是分布式和集中式相結(jié)合的能源。再者,經(jīng)濟(jì)社會(huì)活動(dòng)密集區(qū)域可利用的再生資源豐裕,基于再生資源利用的新質(zhì)生產(chǎn)力區(qū)位選擇指向經(jīng)濟(jì)活動(dòng)密集地區(qū)。這種物質(zhì)代謝能源基石和資源基礎(chǔ)的變化是我國(guó)生產(chǎn)力布局變化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。因此,把優(yōu)化新質(zhì)生產(chǎn)力布局放在促進(jìn)新區(qū)域協(xié)調(diào)發(fā)展的中心位置,是順應(yīng)新質(zhì)生產(chǎn)力發(fā)展內(nèi)在要求的必然選擇。
來(lái)源:北京日?qǐng)?bào) 作者:楊開(kāi)忠






 掃一掃分享本頁(yè)
掃一掃分享本頁(yè)



















